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更新版
我有两年没回老家了,一年怀孕,一年生娃。最近我妈总说想看我写的文,让我多写一点,她想看。其实我知道,她是想我了。
我不是个恋家的人,但我的故乡----佛坪县大河坝镇,却是一个让我无论何时都牵肠挂肚的地方。
我家小朋友时常学着他爸爸开玩笑地说,因为妈妈是农村人啊。当然,他可能并不知道农村人代表的含义,从他们口中说出来,也多了几分宠溺和“嫌弃”。也许在他们看来,农村人就是可爱的人吧。
大河坝镇坐落在秦岭南边,一个山城里的小镇。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却承载了我全部的灵魂。
猛一下不知道怎样宏观地去描述和形容,用一首歌吧。每次听到谭维维的那首《如果有来生》,歌词总会让我想起我的老家: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
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
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裳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生一个娃娃
……….”
我家不种地,但在离我家不远的外婆舅舅姨妈家都有地。他们家的地方叫沙坪。那里有金黄的麦田,有过山风吹过。每次回到他们那里,都是我珍贵美好的回忆。除了青山绿水,金黄的谷堆,还有他们对我发自内心的稀罕。可能因为我妈是我外婆子女中最小的那个,也因为我妈就我一个孩子吧。
外婆家,亲戚家,当然还有我和我妈的家,让我深深地迷恋那个地方,那一块不起眼的小地方。
想起来真的好快,从小在那里长大,却总共算下来也没多少时间好好地待在那里。
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和我妈就生活在那里。印象中我妈是个漂亮温和的护士,医院上班,却也热闹。那时应该还叫“乡”,大河坝乡。我还是个黄毛丫头。我妈有很多年轻的同事,用现在的话说,是一溜儿的帅哥美女。在我妈在忙的时候,我好似就在她单位里打转。那些年轻的叔叔阿姨常常带我玩。有时还会带我去看电影,就在乡政府的大院里。一块空地、一大张白帆布拉成的银幕、观影席一堆大大小小的板凳、嗑着瓜子、吃着小零食,便给那时的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享受。
我妈上班的地方不大。但医院嘛,总是那样的地方:处处弥漫着消毒水味,到处不是病人的嚎叫呻吟就是家属的叽叽喳喳。有急病人的时候,我看到叔叔阿姨们紧张地抢救,也曾无所畏惧地跟着他们进过手术室看着人家做手术。因为是小地方吧,小孩竟然能进去。虽有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长大后却也没有半点从医的意愿。倒是至今都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种骨子里的敬畏之心。
童年的印象里,在医院家属院,还有很多小伙伴。大家每天疯跑,在夏天的黄昏捉迷藏,藏到花园里矮矮的树Y上,听着蛐蛐叫。半夜几个人拿着手电筒装神弄鬼去吓唬病人家属里有个胆小讨厌的小女孩,把人吓个半死然后得意地跑掉。现在想来,是想笑又特别难忘的开心。
那时上学也很近。几乎不存在接送这一说。跟一堆小伙伴走着路就到了。从学校的窗户都能远远地望到家门。
那个时间段,印在我脑海的,当属上学路上两边草丛里盛开的刺花和刺苔。城里人一定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刺花,长刺的花,却又不是玫瑰或月季。该是一种野花,因为根茎上有刺,所以得此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一开就是一大片,粉粉的,也有白白的。风一吹,那扑鼻而来的清香种带着淡淡的甜,闻得人心里也甜。待到花儿慢慢凋谢,在开花的地方会长出细细长长的苔,就叫“刺苔”,有些像蒜苔。那时的孩子,会把这个刺苔折下来,剥皮,然后吃掉。很清甜,我也吃过。我竟想不到用一种什么水果或蔬菜来形容它的味道。总之,嫩嫩的,有水,咬开是脆的。像莴笋吧,甜甜的莴笋丝。用现在的话说,那是纯天然无添加的味道。
那时上学,可能因为我年龄偏小,又听话,加上老师跟我妈也熟,所以对我也常常优待。所以我也爱上学。
我妈那时绝对是个潮人。至少也是个讲究人儿。记得她跟几个熟知的阿姨总是凑在一块讨论时下流行的裙子或布料。记得那时在大河坝街上还有一家裁缝店。先选好布料、量好尺寸、选好样式,过几日便可去店里取到成衣。现在看来,这不是私人定制吗,当属高级的代名词。
于我,我妈也是可劲儿地打扮,捯饬。想想那时候,我真是幸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90年代初,我们乡上的资源有限,但这限制不了我妈妈的追求。她总是托人从县城里市里捎带一些好的东西回来:漂亮的粉色背带裙、白色公主衬衫(大圆盘领带着镂空绣花,喇叭袖)、精致小巧的耳钉、耳环。从佛坪县城发往大河坝的班车里,一度常常载着我的期盼。
我妈还亲手给我织毛衣裙子。毛衣一样的裙子、裙子一样的毛衣。写到这里,我也忽然意识到我的童年其实是又美又潮又幸福的。
还有一个细节。那时一下雨,家长们就成群结队地去给娃送伞,送雨鞋。不知为啥出门都没带伞。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总是如坐针毡地偷偷往外瞄,瞄到自己家长了,就一阵激动和窃喜。我也不例外。每次看都我妈拿着我那把彩虹色的小雨伞,拎着那双绿色的小雨鞋,心里就好踏实。有时我妈忙,来不了,就托别的家长带过来。但无论怎样,那把彩虹伞和绿色雨鞋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在我妈跟前的时光,大抵就是这样。很快,上完了6年小学3年初中。初中毕业就要去外县上高中了,因为家人都觉得那里教育质量高。
于是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就在年,那时我才13岁。高中就在邻县---洋县。车程2—3个小时。但在那时的我看来,那是好远好远的距离。因为要住校,几个月才回一次家。几个月啊。高中时代的学习压力自不必说,从那时开始还要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每天从书堆堆里爬出来,回到出租屋又一头扎进题库里。
那些日子,每次梦到最多的,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大河坝。梦里那金黄的稻草垛,那沁人心脾的稻香。
还记得那时每年秋天,8、9月份,补完课可以回一次家。迫不及待地从洋县三运司坐上发往佛坪的班车。刚出洋县,就看到沿路两边农民伯伯晒的稻谷:金黄色,一粒粒、一片片,一直沿着道路的方向蜿蜒。稻谷粒旁都清一色摆满了啤酒瓶子,一个挨着一个,形成一道围栏。用来保护稻子不被过往的车轮碾压。一路走过,那扑鼻而来的稻香,让人沉醉。那个时间还有月饼和初秋的新橘子。青橘子的味道,只要一剥开皮,那香味就溢了出来。所以我至今都喜欢青橘子,那也是家的味道。
那几年,回家的次数都数得过来。平时上课,放假还要补课。每次回家,我妈都趁着时间做各种好吃的给我。临走又是大包小包。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第二天的班车去上学,头天在家收拾东西。收拾得七七八八了,我妈照例又塞给我一把钱(那时几百块就能用好几个月),让我数数。我接过来心不在焉地数。数着数着,豆大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摔在钱上,渐渐模糊了视线,怎么也数不动了。隔壁有个小妹妹很有意思,她是邻居家的女儿,比我小十来岁,也就是说那时我14她4岁。发生刚刚那一幕的时候,小妹妹刚好在场。她特别纳闷、特别好奇、特别不理解地跑回去问她妈:“为啥阿姨给姐姐钱,姐姐还哭了呢?”呵呵,小丫头,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
高考------漫长的3年高中呼哈哈的生涯,告一段落。下一站,去西安上大学。
花一样的年龄,17岁。从老家的小县城去到省城大城市。来往如织的车流人流,灰蒙蒙的天空,嘈杂的车声人声,到处弥漫着汽车尾气和属于大城市钢筋水泥特有的味道。
怀抱着梦想,在那里遇到了我至今都视为珍宝并受用一生的财富---我的4个大学室友,我们自诩“四小强”。
上大学就在省内,时常可以回家。我也是一放假一有空就回家。车程才4、5个小时,我也长大了翅膀硬朗了很多,觉得那个距离,真心不远。
印象最深的那次回家,是回去做阑尾炎手术。还有四小强中的周改霞陪同。五月的天,手术很快就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回家休息。算是休病假吧。清楚地记得那时刚刚开始流行超级女声。年,是超女的第一年。我妈、我、还有周改一起看超女,好欢乐。李宇春,那个能折腾的假小子脱颖而出。还有很多海选选手,爬到桌子上,站到凳子上又唱又跳。那段时间,我每日吃饱了就睡。躺在沙发上,开着门,有凉凉的风吹进来。时而睡着、时而清醒。就那样安静地待着,心里那个踏实,也是家的感觉。
四年大学因为享福,在青涩、美好、迷茫、混沌中很快过完了。毕业签工作到了深圳。
21岁的大好青春,从内地飞到这个南方沿海大都市。矮矮的蓝天白云,湿热的天气,和一张张年轻活力行色匆匆的面孔,让我对这里充满了期待。
一起毕业过来的有十几个同学,虽然不同校,但从西安过来的就都是亲人。那些年大家都单身,周内一起上班,周末一起出去玩。第一次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跟热情洋溢的同事沿着海岸线骑双人单车。小黑裙沙滩裙、太阳镜,打着水枪拍着照。夕阳下踩着海浪,烤着烧烤,坐在海边聊着梦想,说着憧憬。一堆年轻的男男女女,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
我一度评价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真的。那个时期的心态是放开的。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经济开始独立了;另一方面,曾经纠结伤感的事情都被暂时清空了。年轻如我,活出了一些自己的朝气和轻松。现在看来,是要感谢这座城市。感谢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包容。
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被南方肥沃的绿植包围的城市,心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老家的思念。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陈楚生这位本土的歌手,贴切地描述了每个来深圳打拼的人,心里的感受。
是啊,这里很美,但它没有四季,冬天没有雪。对于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以及“农村人”来说,没有冬天没有雪,每一年都是遗憾的。我怀念冬天怀念雪,怀念儿时的那些冬天,在外婆家过的寒假。
外婆家的院子在沙坪,有鸡有猪,有自己种的菜和苹果树。冬天就跟外婆挤在一个被窝。早上很早外婆就起床了,生好火等着我们起床。冬天的早晨冷得滴水成冰。为了我起床容易一些,外婆总会把我的棉袄和棉裤拿去火上烤热了,合拢、然后再捂着一路小跑过来,递给还在被窝里的我。外婆个子不高,喜欢穿一身蓝色大襟衣裳,戴个黑色帽子,小小的身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定格。我童年印象里,最好吃的是外婆炒的土豆片。那是比现在孩子爱吃的酸奶、蓝莓味的QQ糖、鳕鱼、烧鸭、鸡翅排骨肯德基麦当劳披萨都好吃一百倍的东西。外婆的灶台有些高,半圆形的灶台上架了两口锅,很大的锅。那时炒菜是在米饭空起来之后进行。米饭空在一个竹篮(俗称筲箕篮篮)里,下面接一个钵子,专门接米汤。用高粱绑的刷子刷几下锅,然后放油开始炒菜。放的清一色是猪油,在锅里吃吃拉拉的烧热,怎么就那么香。土豆片下锅,翻炒。看似普通的菜,我机智灵巧的外婆会在炒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撒一把辣椒面进去,有点呛,但瞬间散发出一种焦辣辣的香,别有一番风味。那味道,就那样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一辈子最温暖的回忆,像一坛老酒,越酿越香。
外婆家第二好吃的是烧芍(烧洋芋)。冬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生火。我们好多小孩:我、舅妈家的哥哥和姐姐,围着火坐下。一边烤火,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响。我们在一旁的灰里做好埋伏:土豆和红薯,就是洋芋和芍。一边烤着火,一边聊天,有一句没一句的。在这暖和的气氛里,期盼那不一会儿就可以吃的美味,那感觉,现在想来,就叫幸福。
外婆家还有一绝:腊猪腿,我们叫猪脚棒,人间美味。每次我妈带我回沙坪,外婆就会上去二层的阁楼捡最好的瘦肉给我们做。那个忙碌矮小又麻利的身影,在告诉我们,美味在等。记得二舅妈最喜欢用一种罐子,对,叫吊罐。头天晚上把洗净切好的猪腿放进去,加上萝卜块,用火坑的小火慢炖,直到第二天早上,满屋子飘香。那真是一种不用油不用盐的香,油是肉自带的油,盐是腊肉自带的盐,原汁原味,冬天里饿的时候来一碗,香到无法言说。所以我对家乡的思念,对外婆家的回忆都跟吃分不开,吃货本性吧。
虽然怀念,可惜外婆已经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在了。于是我这些年时常做梦会梦见她。我想如果有机会回去,我一定还要去那个被竹林包围的尚家梁再住几天,一定要的。
最近的一次回家是那年大宝贝两岁多,带回去看姥姥。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坐在我妈门前那个院子里,安静地看两集甄嬛传。至今我还是这想法。闻着鲜花的味道,吹着凉风,或坐或站,没人打扰,拿个pad安静地追剧或是静静地坐着发呆都好。
在我有空能抽身回去的时候,实现这个小愿望。
对家乡的追忆,写不完也道不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我时常庆幸自己是个“农村人”。因为我有过那些原始而朴素的经历,那些最简单的味道却深深地丰盈了我的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绵长的温暖。我从小没有经历大城市的便利、先进和热闹,但这不妨碍我用心去感知。感知我妈在那一对对红色桃心镶钻的耳钉里倾注的期待;感知外婆在下雪的早晨迈着碎步拿来烤得热乎乎的棉袄;感知那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迎面而来的稻香夹着青橘子香;感知每次回姨妈舅妈家大家对我的亲热和稀罕;感知在我后来的人生中遇到和正在遇到的,那些跟我一样真诚而温暖的人。
人们都流行高大上,有闲有钱的时候要去法国去欧洲。而我,一有闲一有钱,首先要去的,是回到我心中的小镇----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
亚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idnhm.com/wazz/11222.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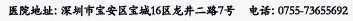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