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甸往事ll杨文阁菩萨手中那棵柳
大夫门前过,先得让个座,不是值钱宝,也是冷热货。
这是民间老百姓对当大夫的人的一种尊崇。
大夫和郎中原是古代官称,带品之爵,始自宋代,后被人加身于行医者,流传至今不衰,可见人们对从医之人的敬慕。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医院老院长高启纯。年的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一,他因医源性感染慢病毒脑炎去世,说明白了就是在长期的手术过程中因某次感染而埋下病患,这种病也叫职业病,潜伏期最高可达30年。
那年他72岁。
那天雪压江山。
72年的风雨岁月里,他行医55年,医治者大多都是林甸人。他的脚印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在林甸,大人孩子谁不知道高院长。
有的人活着,都没人去问。
有的人死了,我们还想着。
因为他是好人,他做了太多的好事让我们无法忘记。
这55年中他到底救治了多少病人,恐怕就是他活着也无法记清。多少个家庭因他而完整,多少生命因他而延续,多少人因他而解除病痛重新生活。
他不记得,而人们都记得。
他的72年人生在平凡中伟大,犹如撒下的万颗花种在我们林甸的大地上烂漫开放。我们想问,敬爱的高院长您是其中哪一朵?他的灵魂犹如星瀚群中的一颗星,我们仍想问,敬爱的高院长,您是其中哪一颗?
茫茫虚幻里您是菩萨手中那颗柳,普渡众生。
现实生活里您手中的那把手术刀救治了多少人的性命。
医生,生命的再造者,死亡路上的拦路神,万丈深渊抛下绳索的人。
老院长,林甸人民怀念您!
年11月,他生于辽宁省的辽阳县高立堡一个农家院里,后因家境贫寒在爷爷的带领下举家来到黑龙江的克山县。
他15岁参加抗美援朝医士班,因为年龄小而被留在丹东后方学习战地救护。国家是想让他们这些孩子兵长大学成后再赴前线。
在学习期间,战事平息,他们转场后方学医。
他们坐了半个月的火车来到了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学习外科。
年毕业后,他连同两个同学一起分配到了省卫生防疫站工作。
美国人扔下的炸弹让瘟疫流行,防疫灭四害是他们的工作任务,而中心工作就是去各单位收集各单位上交的老鼠尾巴。这时的他们学无所用,三个有志向的同学凑在一起商量后决定去找领导,医院也行。
请求得了批准,因为地方正缺少医生,可指标只有两个,但三个人同心,跟领导说,要去都去,否则不去。
于是,三个人又一起坐上了火车来到了齐齐哈尔,又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泰康县,再换乘马车走了两天来到了林甸县。
那年他十七岁,医院当起了医生。
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生病检查期间,北京医院的专家问他从事什么工作。
他说:“我在县卫生局工作。”
专家质疑说:“按理说,这个职业与你的病不符。”
孩子们说:“父亲是外科医生,从医五十多年。”
专家又问:“外科哪一种?”
孩子们回答:“医院外科分不那么清,哪一种要看患者的病情来决定。”
专家明白了,艰苦的条件下,你是全能外科医生。
“这就对了,这种病叫衣原体感染,你的病来源于你的职业,说不定哪一天你做手术时碰破了手。”这是北京专家下的结论。
北京回来后他拒绝治疗,他说:“不要浪费钱了,我是医生,我知道这种病根本治不了。”孩子们哪里肯做,倾家荡产也要为父亲治这个病。
为了这,他最后想到了自杀。
人到了这个时刻,真不知他的心有多痛,那些日子老院长是如何度过的。
有人说,生身之地即是故乡,埋骨之所就是故里。
老院长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林甸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他是在解除病痛中走完自己平凡而伟大一生的。
医院条件十分艰苦,他却有两次离开的机会。
年,他考上佳木斯医学院医疗大专班,从眼科转学外科,因为成绩优异,学校决定把他留校,但因他是带职上学,留校需要当地政府和原单位同意。为了留下他,学校愿意用三个本科学生与他对换,正商磋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建议他借此留下,而他却毅然回到了林甸。
第二次是在北京医学院进修。全国著名的医学外科薛主任看好了他的手诊技能,薛主任的爷爷原是东北王张大帅的随军医官,薛主任本人在北京也有极高的威望。
薛主任对他说:“你可以留下来,只要你本人同意,调转手续我让人来办,爱人和孩子医院工作,你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当地政府和单位同意。”
多难得的机会,他动了心。回来后马上找领导,找单位,说明原因,请求同意。
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但他说:“我们一个医院的医生能被北京医大看中是我们的荣幸,医院去是你的骄傲。医院里人才济济,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在我们这里就你一个,县里培养了你,全县人民盼着你回来为他们治病,这里更需要你,你会舍得扔下他们一个人走了?你能吗?别让他们伤心,别让组织失望。”
领导的话让他落泪,他长叹一声,一夜未眠,最后选择了留下,从此再不提调走的事。大概从那时起他就下定了决心:生在他乡,死在林甸。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
他对孩子们说过,“你们没过过苦日子,如果你们过过那样的日子,你们才能知道共产党有多好,社会主义有多好。当年你二爷临死前你爷爷买了一个烧饼给他,你二爷一辈子没吃过烧饼,他挣扎着吃了下去,吃完就死了,那日子穷啊!咱得知足啊!”
在他的家里有一套齐整的锅碗瓢盆、饭盒。医院里的一些患者准备的,他手术后的许多患者都吃过他送的饭。他常说,“这些个农村来的病人,家里困难,术后需要营养,别的没有,小米、鸡蛋糕的咱还办得到,也就费点功夫。”有时他忙,就让孩子们送过去,常常感动的那些患者泪流满面,病不治已好三分。
他们说,高大夫人好,心好,是咱自己家的大夫。
孩子们记得,有一年一个大庆油田指挥部的干部因大雨断路回不去大庆,半夜里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排气后,家属不在,高院长就为他煮了小米粥送过来。
第二天查房时他发现小米粥只吃了一点点,他问那个人小米粥不好吃吗?
那人不好意思的说:“我是南方人吃不惯小米,要是大米就好了。”
高院长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为他煮了一周的大米粥,那时的大米十分紧缺,一家供应就那么几斤。
这年的三十晚上,全家因此没能吃上那顿大米饭。
那个患者出院后常常打电话过来问候感谢,就这一点他就知足,他就高兴。
还有那么一天的晚上,刚刚下班准备回家的他,突然被一个推门进来就跪下磕头的人吓了一跳。
那人跪在他脚下,声泪齐发的说道:“感谢高主任救命之恩。”
他扶起这个人,只觉面熟并不记得他是谁。
原来他是花园公社某大队的一个农民拖拉机手,一天开车时与另一台车相撞,当时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医院时人已处于垂危状态,生命只有一点体征还在。
这时有人劝高院长说:“这个患者救活的可能性极小,万一死在手术台上,单位、个人荣誉受损,家属也有可能闹事,那样影响可就大了。”
这时的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现在说这些叫没人性,不要忘了,我们是医生,而他还活着,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们面前,我是主任,有什么责任我来负。”
结果这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面前跪地磕头的这个人。
大儿子清楚的记得父亲一生的习惯,行医时近了骑自行车,远了坐公共汽车,从不麻烦谁找车送他一回。
可在家里要搬上楼的那一天,他突然对大儿子说:“给我找台车,要能拉东西的那种。”
父亲终于求他一回,大儿子高兴的开来了收费所的客货两用汽车。
父亲告诉他说:“把咱们的旧家具,包括饭桌子都装上,我要送到农村一家去。”大儿子心里嘀咕,农村没有这样的亲戚呀!可他不敢问只管装。
当车开到花园的一个村子时,父亲找不到要去的人家,东问西问的才找到。
下了车,父亲亲自搬东西,还帮助一件件的摆好,那样子比自己家搬家还高兴。
因为这家人家是父亲的一个患者。
当这个患者出院后,他给父亲送来了两只大鹅,父亲百般不肯,那人哭了,说父亲嫌弃他脏,说他家里非常的干净,干净的满屋子什么都没有。
父亲收下了两只鹅,也在心里欠下了债,所以他一直记着“家里什么都没有”这句话。
从此,这家人有了全套家具,包括一个饭桌子。
那天,全屯子人都来看热闹,有人认识那拿医院的高院长。
医院是患者的再生之地,是生命之火再次燃烧起的火种,但对于患者,医院里充满了恐惧,因为生命宝贵,因为人们珍爱生命。
无影灯下,手术刀前,有多少人不是因病而死,而是因吓而亡。
可能他更了解病人的心态,所以每次手术前他都会轻声细语的对术者说:“不要怕啊,没有事,人都会有病,治了就好了,我给你做手术咱俩配合好,几天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大不了留个疤。”
这是天使的回音,是生命的呼唤,是菩萨圣瓶里的水,犹如细雨润泽人的心田。
这就是老院长高启纯的德行,如同他的名字。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碎的人,一个能启迪人心灵与生死的人。
他在患者出院时常常这样说:“我是医生,可我不希望大家来这里,走了的就别再回来,回家健健康康的过日子。”
年,组织上信任他,老百姓相信他,医院的院长,但是在他看来自己首先是一名医生。他离不开那把手术刀,他仍然出入手术室,亲自为患者做手术,他医术高,人热情,没架子,大伙都找他,不用走后门。
院长一职对于他来说只是更忙了,更累了。
每医院,不去的话他睡不着觉。
巡视、查房、询问患者病情是他每天必须要做的,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生。
父亲当了院里的一把手,儿子自然想要借点光,挣点钱,这也是人之常情。
头脑灵医院用煤,医院大,一年能用上千吨煤,每吨能赚几十元,不小的一笔收入,但他明白,这事必须瞒着父亲,知父莫若子啊!
于是,他来了个迂回政策,偷着去找分管后勤的院领导。
这事很快办成了,可父亲也知道了。
儿子也是第一次领教到了父亲的恼怒,没有了往日的慈爱与温和。他永远忘不了,父亲拍着桌子训斥他,“这煤谁都可以进,唯独你不行,如果我不是院长,你能办成吗?你不能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是院长。”
虽然发财梦破灭,还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不生气,他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医院的事,孩子们知道的不多,因为父亲回家从不提单位的事,也不准家里人问。他说:“家是家,单位是单位,分不清就乱了。”
他医院前面的小二楼上。孩子们都记得常常夜里有人爬上来敲他们家的门,开始害怕,后来习惯了。而每次听到敲门声,父亲马上穿衣起床,医院。
父亲说过,“人家相信我才来找我,我是医生,我最知道有病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咱拿人心比自心,谁不有病谁不知道哇!”
他总说,“我先是医生,后是院长,手术是我的责任,有病哪分白天黑夜。”
妻子张晶莹是土生土长的林甸人。她也是外科医生,于年因肝癌病逝在家里,那年她才59岁。但她这一辈子不后悔,因为她有一个值得她骄傲的丈夫,如果说后悔,那应当是没能陪他到最后。
这许多年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家里单位,她都支持着丈夫,男人的成功一半来源于家中的女人。
即便当年日子十分艰苦,即便丈夫偷偷瞒着她把工资替患者交了住院费,即便丈夫悄悄的拿家里的东西给患者,她都微微一笑,没有任何埋怨。
天下事有时奇,天人下有时怪,什么人找什么人,真正的夫妻患难与共,福乐同享,心脉相通,如同天地经纬,林中猴头,找到哪一个,另一个就不远了。
妻子的过早离去,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打击,那种痛苦与绵绵思念只有他自己清楚。
孩子们大了,他要担当,单位事重,他要负责,不知有多少夜晚,他独自遥看灿烂的云海、星河,追寻妻子当年的身影,仿佛彩云间、穹顶下,妻子正声声呼唤,让他保重自己。每一次他一定会热泪奔涌,心如潮来。
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按照当时他的身份和条件,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陪伴没有?可他选择了独守,那是他对妻子永远的爱恋与忠诚。
有些事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他把这些深藏在心底,用忘我的工作来压制心里烦闷,手术刀、手术室、无影灯、患者能让他暂时忘却。
医院是他另一个家,患者是他最亲近的人。
他也时常伫立在办公室的窗前,焦灼万分的思考,医院条件差,技术水平低,资金设备短缺,很多患者异地救治,也有抢救不及时的时候。
为了解决这些,他一次次的跑省、市,跑政府,医院条件。
死亡者家属的哭声,也让他那颗善良、仁爱的心多掉许多泪。
也有那么一天,屋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半夜里他最害怕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而这样的电话他一生也不知接了多少回。
听筒里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哭求声:“叔叔,我爸爸疼的在地上直打滚,求你救救我爸爸……”
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农村远处的患者,外面正风急雨猛,他慢声柔情的说道:“孩子,别急,慢慢跟叔叔说,你家在哪里,我马上去救你爸爸……”
那天夜里,他们坐了一半的车,走了一半的土路,在那个患者的家里就地做了手术,急性阑尾炎也能要人的命。
天亮他们才回来,大雨浇的他感冒了一个星期,人瘦了一圈。
每做完一台手术,从手术室里出来,他都高兴万分,每次都有一种成就感。
终于退休了,孩子们特别的高兴,父亲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当然,孩子们也有另外一种打算。儿子劝父亲说:“咱也开个诊所吧,普通大夫都开发财了,以你的医术和声望,不怕挣不到钱。”
他踌躇之后答应了,但约法严格,开诊所不手术。他认为,小小诊所不具备手术条件,不能为了挣钱,什么都不顾。
“不手术也行,”儿子说:“咱就卖药,也一定比别人家卖得多。”
但结果这个诊所还是没有开成。
儿子说:“医院的院长跟我爸都说了些什么,反正父亲变卦了,诊所不开了,医院当了专家。”
父亲就是父亲,孩子们能怎么样呢?只能任由他去,父亲自有父亲的活法。
医院期间,有人发现他经常背着一个帆布做的兜子,并常常去一家卖林甸鞋的商店,买了一双又一双。
他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一起谈笑,就有人偷偷的去翻他的帆布包,发现那里面不但有鞋,还有衣服裤子。
大家问他背这些干什么?
他反倒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我的工资一个月好几千,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工资,一个月一千够花了,剩下的买些鞋、物送给那些家里困难的患者,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也能解一时之难。”
大家无语了,脸红心热,更加尊敬这位老院长。
去世前,他叫来了几个孩子,掀起他睡的木板床,在床垫下的塑料袋里拿出三本存折,两本是他和爱人的工资折,一本是存款折。然而,两本工资折里只有五千块钱,存款折里也只有三万块钱,这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积蓄。
他说:“就这些了,你们留着,谁困难谁用,人是要靠自己的,不能靠父母。”
是啊!他没有留下大笔的钱财,却留下了永远都用不完、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品德、慈爱、善良。
在他病重期间,看他的人80%他都不认识,而人们认识他。
电影公司的老苗来看他,拿出50块钱,说:“高院长我就这一点心意,感谢你过去的帮助。”
病重的他百般不受。
老苗哭了,他说:“我明白了,你这是嫌少哇!我回家再拿点。”
高院长也哭了,他点头留下。
老苗走后,他说:“你苗叔家人口多,工资少,日子过得困难,找机会把钱还回去。”
他的病急剧恶化,九天前他小跑着上楼去检查,十天后两个儿子搀着父亲上楼都艰难。
他是医学专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病情的严重性。
有一天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他最后的嘱托。
这时的他已是拿东忘西,说话断断续续了。
他对大儿子说:“人总是要死的,我并不怕死,你妈走了9年了,我也要走了。回想这辈子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现在我有四件事交待给你,本想多写点,可手不好使,说完就忘,就这四条吧。”
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这张纸条孩子们至今还留着,这是父亲给他们留下的永久纪念品。
四件事分别为:
1、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近60年,医院,你妈在家走的,医院走,医院里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长,我从那走心里安宁,医院。
2、丧事从简,不要惊动、麻烦任何人,如果可能,你们几个把我发送了就行。
3、和你妈的骨灰并在一起,只要在林甸,埋哪放哪都可以。
4、骨灰盒我要四块板,这是咱中国人的传统。
之后他问泪流满面的大儿子:“我说的话你能不能做到?”
儿子哽咽着说:“爸,等真有那么一天时,我一定做到,但你现在先别说这些,咱治病要紧。”
这之后不久,他就深度昏迷不醒。
长时间的昏迷让家人万分焦虑,大家心里都明白父亲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大孙女来到了爷爷的病床前,哭着呼唤着爷爷,而这时他竟奇迹般的睁开了眼睛,无限疼爱的伸手摸了摸大孙女的手后再度昏迷。
小孙子来到了爷爷的床前,家人是想让幼小的孩子最后看一眼爷爷,希望他小小心灵里记住爷爷的模样。可是,爷爷那张苍白憔悴的脸已十分难看,家人害怕吓着孩子,看一眼后便要抱走,这时他竟再次醒来,深情的看一眼小孙子,眼角一滴浑浊的泪慢慢流出,从此长眠。
亲情如此的神奇无比,能让地动山摇、人苏命醒。
好人一生不平安,多为他人着想,一生操劳,别人伤心,他也落泪,如何平安?
那一天,他走了,带着对林甸这块热土的无限眷恋,带着对亲人、朋友、同事的无限祝福,带着对他追求奋斗了一生的卫生医疗事业的美好向往轻轻地走了。
那一天,雪压冬云,春来大地,他将在天国的长生树下永生。
西去的列车开上了九霄云外,停靠在天堂的门口,人间判官为他盖上了一枚大大的“优”字。
从此,天堂圣殿里多了一位白衣圣神。
天巧地合,人间万象,有人想起几十年前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在林甸的大街上狂奔乱语,他卖刀卖米不要钱,说:“菜刀百元、小米十元时我来收钱。”
也有有心人记下了他说过的暗语:
一方营盘,坐北朝南。
八八六十四方块,布局子午线。
三十七度故事,专讲林甸。
虽说小县,当出圣贤。
校出人杰,府出高官。
仁德之人,医院。
头顶寒雪,脚踏热泉。
道如长虹,横来竖穿。
是与不是,生者自见。
小二试问,见在哪天?
天机不漏,泄而有险。
菜刀一百,小米十元。
万般奇相,应在百年。
高院长去世这一年,正应大祁店挂幌百年之期。
杨文阁
转载请注明:http://www.idnhm.com/wadzz/12469.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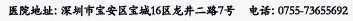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