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塚敬节医案一则有感
一天,有位友人来访,商量一位阑尾炎患者的治疗。该患者已使用大黄牡丹汤十天,体温在39.0℃上下,仍有腹痛。详细询问病情后,感觉到病灶好像已化脓,已经不适宜再用大黄等攻下了,我便建议试用薏苡附子败酱散,但使用该方三天病情仍在恶化,便医院诊察住院的患者。患者为一位二十五岁身体健壮的渔民,虽然躺在病床上呻吟了十余日,但肌肉尚壮,营养状态也未见严重衰脱,仔细观察时发现有轻微的黄痕倾向。我走进病房时,患者在用水漱口,润湿嘴唇后再将水吐出。当问及是否口干时,回答说嘴里很快就变得很干燥,连舌头活动都困难了。观其舌象,舌头如同剥脱了一层皮,发红,并且干燥。脉洪大数。该日上午恶寒,从下午起,体温上升至38.0℃以上,无汗。腹诊,皮肤干燥,右下腹略膨隆,回盲部对按压敏感。右腿不敢活动,稍加活动则牵扯腹部疼痛。小便发红、浑油,排出不通畅,大便不能自然排出。午后手足烦热,欲伸到被子之外。以上症状中,有《金匮要略》所云“脉洪数者,脓已成”的表现,所以泻下剂是禁忌。另外,口舌干燥,不欲饮水,只用来润口,手足烦热等,为使用以地黄为主药方剂的指征。基于这些考虑,便决定用下面的方药:即七贤散与八味肾气丸。七贤散出自《外科正宗》,可以看作是肾气丸的变方,即肾气丸去桂枝附子泽泻加人参黄芪而成,这两个方剂均以地黄为主药。七贤散主治“肠痈溃后,疼痛淋漓不止,或精神减少,食不知味,面色萎黄,自汗,盗汗,睡卧不安”等,正对应该患者之证,再加上八味肾气丸,如虎添翼,二三天后病情肯定会减轻的。如果这样的病都治不好,那可如何是好。于是便自信满满地返回了。可是,服药二天后,却出现了大问题:第一,全身大汗出,终日不止。第二,出现散在性感觉异常。第三,右脚内侧出现轻微痉挛。第四,脉变弱,幅度变窄。并且已有的恶寒、发热、腹痛、手足烦热、口干等症状依然存在。结果很明显,病情加重了。于是根据“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一条,作为最后的一张牌,决定使用四逆汤,并加上人参茯苓,投予了茯苓四逆汤。出乎意料的是,仅服药一天,感觉即变得爽快,腹痛减轻,腹满消失,也有了食欲。服上方十天便痊愈出院了。老陈评注:这个医案非常得详细,生动地刻画了每一个临床细节,非常有现场感,同时,一波三折的病情变化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当然,本案在临床方面有相当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下面我谈一谈我对这个医案的一些看法。1.在最开始大黄牡丹汤无效,大塚敬节先生考虑疾病已经化脓,不适合用大黄攻下,于是建议薏苡附子败酱散进行治疗,可见他区别两方的点在于条文中的“是否成脓”,历代有部分医家认为不应当只以这个方面来区别,应当结合药证、体质方面来鉴别,《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中认为薏苡附子败酱散用于无热,体力衰退,腹壁软弱,脉弱的肠痈证,但细看此患者,虽然患病十余日,但肌肉仍然强壮,体能也没有损耗,并且还有发热的倾向,所以大塚敬节在还没有见到病人的情况下,在电话中开具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应当是误治!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很多人对肠痈病的经方,脑子就只有大黄牡丹汤和薏苡附子败酱散这两个,但实际上中间还有很多状态的方剂需要我们考虑,矢数道明认为如果使用大黄牡丹汤症状加重,或者炎症和化脓较轻,症状不是很严重者,可以用《千金方》之肠痈汤,此方为大黄牡丹汤去大黄芒硝加薏苡仁,汉方使用此方常加芍药。另外,从腹证上来看,大黄牡丹汤和薏苡附子败酱散都有右侧少腹部压痛,同时都有大便秘结、里急后重的表现,我们还需要想到桂枝加芍药汤,此方在《腹证奇览》中也提到有少腹压痛,经常被用来治疗里急后重的痢疾病。所以这里我们应当避免腹证方证的简单化,应当不断地充实相类似的方剂,这才是我们汉方家所追求的!2.大塚敬节在详细诊察后,认为口干舌燥,不欲饮水,手足烦热为使用地黄为主要方剂的药物,基于有恶寒阴证的情况,使用了肾气丸的方剂。这种思路是先确定药证,然后再去筛选最合适的方证,在汉方医学中很常用。根据吉益东洞的看法,地黄的使用指证是烦热、脐下不仁和悸动,这个患者午后手足烦热,欲伸到被子之外,符合“烦热”表现,但肾气丸我感觉有这么几点不符合。第一:患者年龄、体质不符合,肾气丸在汉方中常用于60岁以上老者,并且其体质一般是体能低下,瘦弱,从《金匮要略》条文“虚劳腰痛”就可以看出使用肾气丸的先决条件要符合体质。第二:小便不符合,肾气丸小便一般都是夜尿多,尿频,或者小便少,但一般不出现小便发红的情况。第三:腹证不符合,肾气丸的腹证最常见少腹不仁和肚脐下正中芯证,且全腹腹力较低。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使用肾气丸无论是从体能还是腹证来看,都不太符合。3.患者服用肾气丸合七贤散后,出现了大汗不止,脉弱,明显已经陷入阴证四逆汤的状态,这里很有意思!因为纵观伤寒论条文,四逆汤证一般都是使用汗法、下法、吐法等攻邪之后,水液大量丢失而造成的,但此患者却是使用了补虚的肾气丸后,却出现的少阴证,这里是药物的关系还是疾病本身的发展呢?从疾病发展史来看,前面十五天病情都呈阳性变化趋势,但在是用肾气丸2天后,病情迅速反转往阴证转化,所以这应当也有药物的因素在里边,可见临床上不一定都是墨守成规,使用补剂后也有可能导致三阴病的形成。4.我们看误治后患者的表现:全身大汗不止,脉弱,仍发热,恶寒,腹痛,手足烦热,口干,脚微挛急,便秘,舌象还是干燥的,这个地方大塚敬节使用茯苓四逆汤看起来好像很得心应手的样子,但我感打赌我们大部分医生看到这种即便是大汗出不止,脉弱的患者,也不敢用四逆汤,为什么?因为四逆汤证一般都是手足厥逆、下利、苔润、腹部软弱的,但这个患者手足烦热的,大便秘结的,口舌干燥的,腹部有压痛的,基本除了一个大汗出和相对的脉弱之外,与典型的四逆汤证都不符合,我们在医案中可以看到一段话,“于是根据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的条文,决定使用四逆汤并加上人参茯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塚敬节先生只看到了这几个证,而对于其他矛盾的症状他似乎有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在汉方中很常用。汉方家在针对一个症状进行方证辨证取不到效果时,往往都会先把这个症状暂时掩盖起来,而选择其他的症状进行处方,矢数道明曾治疗一25岁男子,数年来每日下利3-4次,食欲不振,恶心,全身倦怠,胃内停水,根据下利为主证,连用茯苓饮、六君子汤、断痢汤、人参汤、参苓白术散、桂枝人参汤均无效,于是便不管下利,只根据恶心和胃内停水为主证,投小半夏加茯苓汤,结果诸症痊愈。这个医案大塚敬节估计用的也是这种思辨方式。我们国内受脏腑、五行的影响,总喜欢面面俱到地想把全部症状都分析个明白,这种方式的确很稳妥,但有的时候也会成为绊脚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临床症状时,有时候选择性的“失明”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回过头来,大塚敬节前面的方剂都是针对手足烦热、口干、腹部疼痛、化脓炎症,而最后只针对大汗出和脉弱,使用茯苓四逆汤,也就不难理解了。5.患者的情况恶化是在使用肾气丸之后出现的,那我们复盘一下,在使用肾气丸之前的患者,该使用什么方剂呢?下面是我的思路:(1)如果根据阑尾炎疾病谱和腹证来考虑,使用了大黄牡丹汤无效,而患者体能也不是很虚弱,同时还有炎症和热象,应当使用肠痈汤。(2)如果根据手足烦热,舌头剥皮,发红干燥,小便发红浑浊,大便秘结,三物黄芩汤也有使用的可能,但患者上午恶寒,下午就发热,无汗,好像还有一种外感表证存在的样子,虽然没有头痛,也不适合用三物黄芩汤,如果针对这种发热的情况,根据条文“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三物黄芩汤主之”,倒是可以使用小柴胡汤。(3)疾病的排邪途经有三个,分别是汗、大便和小便,大便已经试过无效,如果针对小便发红、排除不通畅,口干,舌红苔剥,下腹部彭隆疼痛,使用猪苓汤去通利小便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患者有无汗,发热,恶寒,好像是个麻黄桂枝的证,但患者有这种阑尾炎的化脓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发热恶寒不能看做麻黄桂枝证,《金匮要略》中肺痈、肠痈都明确记载有恶寒的表现。综上所述,使用肠痈汤是从《金匮要略》疾病分论的角度来看的,而使用小柴胡合猪苓汤是从《伤寒论》疾病总论来看的,如果是我来处理,我可能会先使用前者,当然具体疗效如何不可能得知,不过从这个医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思路,临床好比战场,风云莫测,外行人看起来就是几声战鼓之后,输赢已分罢了,但是其中的奥妙唯有不断地停顿回放才能体会到,用兵如此,用方也如此。陈军帆
转载请注明:http://www.idnhm.com/wacs/13052.html
最新文章
推荐文章
- 没有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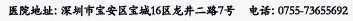
当前时间:
